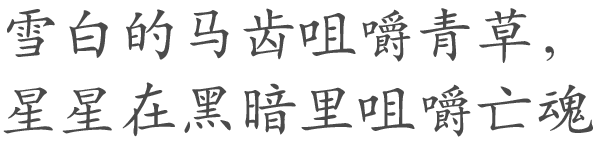中国歌曲的命运及其流转
中国歌曲的命运及其流转
极端地说,中国歌曲与西方歌曲、与歌曲,是两种不同的声音艺术形式。
一
我时常想象古代的歌曲是什么样,因为既没有录音,也没有谱子流传,真是只能够想象。但其实也不尽然,在生活中,我偶然也会有一些境遇,想,古代的歌曲差不多就是我现在听到的这样。
工尺谱是中国最早的完整记谱法。学术界一般认为,工尺谱最晚于晚唐五代已经产生。这个依据是源于,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迄今发现最早的工尺谱——后唐明宗长兴四年(933)写本《唐人大曲谱》,按此推算,加上史书上的文字记载依据,就得出了“工尺谱最晚于晚唐五代已经产生”的结论。
所以,在面对五代以前的歌曲时,研究者也只能想象。有时他们能得到一些线索,隐约知道古代的歌曲是怎样的,但因为没谱子,依据再多的史料,也不可能将当时发生的声音完整地再现出来。
中国最早的歌,于今还能够追溯的,当是时间上不能够准确确定的《弹歌》,这支远古古歌只有8个字,“断竹,续竹,飞土,逐肉”,是一个狩猎场景。我无端地以为,这首歌应该是首号子,以众人齐声呼喝的方式演唱,很干脆地唱出两个字,然后停顿,马蹄声、擂鼓声、节奏声,然后,再干脆地喊出下两个字。
能比较全面地看出古代歌曲面貌的,是《诗经》,诗经中的“国风”,是周代民歌的总汇,包括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北等十五个地区的民间歌曲,即3000年前至2500年前的中国民歌。
这时的民歌很简单,你看诗经中的句子,都比较短,形式也比较的一律。其中有号子、夯歌一类的劳动歌曲,但最多的还是在祭祀田祖或“禊祓”(去河边用水冲身以求吉利)等场合唱的“山歌”。山歌较抒情,可能是当时最复杂的歌曲形式。很多民歌采用了歌与和的形式。公元前685年,管仲在鲁国被俘,鲁国把他用囚车押到齐国去。路上,管仲对拉车的役人说:“我为汝歌,汝为我和。”(见《吕氏春秋》)
研究者们认为,“国风”的曲式简单,但有的在曲尾加上一段,叫做“乱”。乱是什么样的,没人知道,我猜测,这就是华彩与即兴,唱花腔,狂感叹,咿咿呀呀噢噢,跟叙述调没什么关系的。有一次,孔子对鲁国乐官师挚的乱大加赞赏,这段乱加在《关雎》的曲尾。孔子说:“洋洋乎,盈耳哉!”可见这乱的效果。(见《论语》)
为什么民歌叫“风”呢,这可大有来历。风是一种自然现象,而民歌是一种跟风差不多的人类的自然现象。古人想,这种自然现象与各地的水土是密切相关的,各地的水土又影响到人们的声音,包括语言的声调与歌唱的风格特征,所以民歌就叫“风”了。(见吴钊、刘东升《中国音乐史略》)《吕氏春秋》说,“闻其声而知其风”——听到它的歌,就懂得了那里的风;听到那里的话,就明白了那里的音乐;说得多诗意而又哲学!18世纪法国批评巨匠丹纳写《艺术哲学》,演绎出的宏大美学体系,不就是源自这样的一个基本理念?
与诗经记录的中原民歌同时同代,还流传着各边远地区的民歌。
楚歌是边远地区民歌中最知名的。楚歌在演唱技术方面难度很大,你现在看,现在的楚地,比如荆江号子,在演唱技术方面的难度也很大,不过那时候的难度大可能概念还不太一样。当时的著名诗人、美男子、大众偶像宋玉,是众人追逐的歌曲名家。楚襄王有次奇怪地问:怎么士大夫和庶民们最近不说你的好话了?宋玉回答说:“有人在市中唱歌,开始唱《下里》、《巴人》,大家都能够随声跟着唱和帮腔(“唱而和”),一呼而数十人应。而我作的《阳春》、《白雪》呢,能随声唱和帮腔的,没几个。这是因为乐曲的艺术性高了,能欣赏的人就少了。”(见《昭明文选》“宋玉对问”篇)
屈原的作品更神奇,尤其是他对“乱”的运用,极为奇崛。《离骚》中的“乱”,一开头就是三个音的惊叹“已矣乎!”想必极惨,极高,极曲折。《招魂》中的“乱”,最后一句则是“魂兮归来,哀江南”,仅从字面看,也是不胜其哀。
楚声之外,还有越讴、滇歌。
越是今天的东南沿海一带,但地域更偏于浙江,而不是它当然包括的福建、广东两地。比如春秋时建立的越国,是以绍兴为中心的。史载越人“俗尚淫祀”,越讴,也就是越民歌,也非常的“淫”,“淫”这个字,古代指的是过分,用指音乐,换个现代词,可说绮丽、冶艳。关于他们的唱法怎么个冶艳法,无一记载,只知道他们的伴奏乐器是很丰富的,有琴、筑、笙、鼓等。可以想象他们音乐面貌的最有趣的一个记载出自《吕氏春秋·遇合篇》,说有位客人见越王,为他奏籁(排箫),“羽角宫徵不谬”,用今天的话说,do re mi fa so la si do都吹得很准,可是越王不喜欢。客人于是改吹“野音”,越王闻之大喜。这除了说明越讴很野很“淫泆”,更可能的事实是,越讴的音符跟中原的五音是不一样的。以中原的观点看,构成越讴的基本音当然也是“羽角宫徵”,但是越人的“羽角宫徵”,其音高却不是那么回事,可能比中原的“羽角宫徵”高1/4、1/5或1/6音,唱起来就像走调了一样,但在越人听来,大喜,这走调了的才是唱对了的越音。
滇歌是云南楚雄、祥云一带的歌,从乐队看,他们的歌只怕比越讴更发达,有葫芦箫、铜鼓、编钟等,唱时载歌载舞,非常热闹。
二
一直到清朝末年,中国都没有出现现代歌曲的样式。
中国所流传的歌曲,一直是民歌、诗词、戏曲,道观和寺庙中还有一部分经文唱诵,它们源远流长,种类、形式繁复,但追溯起来,都能追溯到诗经那个时代。
由于有工尺谱、减字谱记录,这些歌曲不只是可以想象了,今人也差不多可以唱出来。由此可以发现中国歌曲在旋律上的一个巨大特征,无论民歌、诗词、戏曲,其旋律都是依字行腔、曲随字音:粗朴的,就是吟诵腔;精妙的,旋律婉转,但总能落到与歌词读音相一致的调调上,听起来很熨贴自然,像是一种更高级的说话、感情更强烈的文字抒发。
都是歌,为什么要把它们与现代歌曲截然区分,难道它们与现代歌曲有什么不一样?
我猜想,有两个不一样,导致中国古歌与现代歌曲殊异。
第一、中国歌曲时常没有节奏。你现在听一些民间艺人的民间演唱,如果你扎扎实实地去记谱,你会发现你记不下来符合现代音乐要求的谱子。在打谱号的时候,你标不出来是4/4拍、3/4拍还是3/8拍。按现代记谱法的习惯,你当然还是会分出小节,只是一小节与一小节的时值不会一样,长长短短,几无规律。你之所以定出了小节,是因为歌手在这里那里有自然的停顿。在许多歌曲里,中国歌曲就是这么不讲节奏,节奏完全是你自然的气息。
我这么说一定会挨专家的板子。专家会说,有些歌曲也是有节奏的,那个节奏叫板眼,俗话道“有板有眼”,那就是说节奏把握得好的意思。在有些类型的板眼里,即流水板、一板一眼、一板三眼,差不多可以对应现代记谱法里的1/4拍、2/4拍、4/4拍。但根据我的实际经验,还是不太一样,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方式,对节奏很不讲究,尤其是到了散板,随便来,爱怎么着就怎么着。总之,就是不遵循现代歌曲的节奏样式。
第二、有时候,中国歌曲的音高用记谱法没法记,说句大白话就是,它唱的并不是do re mi fa so la si do。do re mi fa so la si do是外来的,咱中国人既不唱这个音,也不唱这个音高。
关于中国歌曲,已经有个国内外共认、差不多已经人尽皆知的说法——中国音乐是五声音阶的。其实五声音阶不止是只有五个音,中国大量的歌曲、乐曲实例已经说明,它以五声音阶为特色,但也包含了另外两个音,与西方的十二平均律一样。
所以,以下这个判断,完全是我不顾权威音乐学的乱猜想,我是从中国现在依然还存在的诸多野唱发现,中国的七音,你如果非说它是do re mi fa so la si,它的音高与do re mi fa so la si不完全是一回事。可能各地不一样,各民族不一样,你若是听那个民歌原汁原味儿地唱,它是有点走调的。我听过苗族的民歌、彝族的民歌,有些很著名,如《小河淌水》、《半个月亮爬上来》,当少数民族用他们的原词原调唱,听起来是有点走调的。
现代歌曲是一种统一的样式,随着它在全球传开,不完全一样的音符、音高、节奏、音乐体系,正在统一起来。
三
现代歌曲是在洋务运动的潮流中到中国来的。洋务运动引入了西方的科学、文化、军事、工业、技术,但很少提及到这么末节的细节——它也引入了西方的歌曲和音乐。
以前是没有学校的,上学只在家里上,叫私塾。洋务运动后开始有了学校,类似现在的学校,时称“新式学堂”。按照西方学校的模式,这学堂是要开音乐科的,于是,现代歌曲在中国出现了,叫做“学堂歌”。
最早的学堂歌,也就是最早的中国现代歌曲,大多是日本歌、欧洲歌填词的,用洋人原来的曲调,填上中国的歌词,教娃娃们、学生们唱,就是学堂歌了。当时盛行的,有儿童歌曲、舞蹈游戏歌曲、摇篮曲、进行曲,在演唱形式上,独唱、齐唱、二声部三声部的合唱也出现了,然后词曲都发自中国人自己的创作也出现了,如当时的学堂歌大家,沈心工、李叔同、黄自,当然,这创作是用现代曲谱的样式,完全合乎西洋歌曲的标准。在音乐的天地,此时已经世界大同。
从洋务运动开始,是一个四海激荡的时期,革新、革命思潮在中国大地汹涌,新创作遍地开花,无法一一分辨其作者。特别是新民歌的创作,一时澎湃,利用旧有的民歌曲调,填上新词,群众传唱。应和着从外界引入的音乐时风,这些民歌已与往昔不同,它是新派的、战斗性的;形式上更规范,易于群唱;创作者是学堂人或学堂人的扩散人群,已经融入或接近了现代歌曲的样式。
四
1927年,黎锦晖创作了歌曲《毛毛雨》,这是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。大上海流行音乐从此发轫,中国流行音乐由此开始。
1930、1940年代,出现了两位歌曲巨匠:解放区的冼星海,创作了声乐套曲《黄河大合唱》;国统区的王洛宾,跑到西域去采风,传出一首又一首传世民歌杰作。
1950至1970年代,出现三位歌曲大家,刘炽、雷振邦、劫夫。十七年(1949-1966)中的新民歌,至今闪亮,光照数代;十年浩劫中的语录歌,成为浩劫的一场配音,但劫夫创作上的才情魄力,并不因那个荒唐的时代一笔勾销。1970至1980年代,又出现了他们在歌曲艺术上的优秀传承者施光南、王酩、王立平。
1980年代至今,中国流行音乐的兴起引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,李泰祥、侯德健、罗大佑、崔健、李宗盛、腾格尔、陈升……群星荟萃,绽放着不同的光彩。中国是什么?问题在继续,答案也在继续。
五
不管哪一个时期,在现代歌曲的历史上,一直有着极土和极洋两种要素,这两种要素碰撞最热烈、光彩最闪亮时,其歌曲就最闪亮,终至成为一个时期最代表“中国”这俩字的声音,成为中国歌曲的时代最佳代表。
学堂歌时期,李叔同根据美国人J. P. 奥特威的曲填了词。如今,奥特威的原歌早已无声无息,李叔同的《送别》却依然在中国大地上传唱。这不是普通的填词,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,夕阳山外山”的歌词,就是中国地地道道的诗词,它嵌进这个曲调的方式,也与中国诗词本身的吟诵方式一致。极土——中国词,极洋——美国歌曲,合成的是,天衣无缝的新时代中国词咏。百分之九十九的学堂歌都没有流传下来,而这一首流传了下来。
大上海流行音乐时期,周璇、白光等一批明星,把黎锦晖、陈歌辛等的歌曲唱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曲。大上海流行音乐的实质是什么?大上海流行音乐的实质,就是中国的戏曲,糅和美国摇摆爵士乐的节奏和配器。周璇的嗓音是戏曲的,她唱的很多歌甚至依然能看到戏曲的原态,这种包裹在时代新风中的传统魅力,传给了邓丽君又传给了蔡琴,至今依然是中国为各种人群喜闻乐见的最大众的艺术。
1930、1940年代,冼星海是个真诚学习民间的学院派,王洛宾也是,他们都受到正统音乐学院的教化,又俯下身来,认真地倾听民间的声音。极土的一面是,中国的民歌;极洋的一面是,现代交响乐、音乐的经典样式、中西合璧的古典配器,总之,西洋学院派。中国民歌由此一役,第一次令人信服地经典化了。
1950至1970年代,刘炽是一个听遍北方各地民歌小调、浑身吸满了民间灵气的红军作曲家,所以他一提笔就是“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稻花香两岸”这样极为搭调的北方话旋律;“烽烟滚滚唱英雄”、“让我们荡起双桨”的谱曲,也是那么顺口。他第一个示范了大气、壮阔、合乎中国口音的旋律制法,彻底突破口白腔而得道升天,而他告诉你经验说,这是化自民歌《小放牛》,这是化自蒙古族的一个小调……
同一个时期,雷振邦通过电影歌曲使《刘三姐》、《五朵金花》、《冰山上的来客》插曲成为中国人久唱不衰的歌曲经典,他炼制这些传世之音的秘笈是,到20多个省、市、自治区搜集民歌,十下云南,六进西双版纳,在他收藏的满满一书柜资料中,每一个省、每一个民族的民歌,都能找到。
刘炽和雷振邦都受过音乐学院的专业训练,学过先进的西洋作曲法,他们的歌曲,也有极土和极洋两面。50至70年代的歌曲创作主流,史称新民歌,实际上传承的是冼星海和王洛宾的衣钵,其精髓是民歌的现代化、古典化、经典化,即以学院派的现代作曲技法,将民间歌曲,提升为更谨严、更博大的歌唱艺术。
土,是中国;洋,是西洋,很多时候代表时风,代表时尚。最容易让当代人明白这种土洋碰撞、土洋拥抱的是流行音乐,它是回答某种音乐、某首作品缘何能够如此轰动的近乎永恒的秘密。
崔健,其摇滚乐的形式完全是外来的,但他的旋律,比如《一无所有》,是典型的中国陕北民歌。他用一种近似于农民的口音演唱,用唢呐、古筝形成配器中的华彩。
腾格尔,是交响乐或摇滚乐坛场上的现代蒙古民歌。李宗盛,是中国口白腔在城市流行乐中的绝妙发挥。
国门完全打开后,当流行音乐的风软吹数年,特别是年轻一代在国际流行乐的时风下创作完全潮流化之后,刀郎突然红了,雪村突然红了。刀郎和雪村是什么?刀郎和雪村是西化的音乐背景下突然强化的中国音调。刀郎等于,在听遍了西式流行音乐的一片空白中突然让你听到中国的歌声,它是摇滚乐+新疆民歌;而雪村相当于,西式民谣弹唱中的中国北方小调。
更近的景观,我们甚至可以思考,年轻而无名的歌曲作者何沐阳,其《月亮之上》(填词)、《彩云之南》、《坐上火车去拉萨》为什么会不胫而走?庞龙显得俗气的《两只蝴蝶》、《你是我的玫瑰花》,不管乐评人多么不屑,歌曲照样在全国爆红?“凤凰传奇”为什么会成为滥大街的神曲组合?
只因为这是我们骨子里的东西。
六
中国是什么?中国就是这,一道在时风中前进的永恒的华人脉搏。 土,代表着根、土地、我们的存在;洋,代表我们生动着、新鲜着,我们活着,我们活在此时此刻。我们渴望着新生,我们向着无穷外界张望,迈开了双脚。中国,我们,正与世界、与发达民族,一起共存,一起共鸣,一起相互运动。
它几乎可以解释中国自与世界发生广泛联系以来,一百余年,在音乐领域里发生的所有显著事实。不信,你可以挑出历代历年的每一例轰动事物,自己试试看。
像三千年前中国人说的,“闻其声而知其风”,风是一种自然现象,而歌是一种跟风差不多的人类的自然现象。它发乎人的内心,并与水和土密切相关。所以,是这样的声音,它被季节鼓荡,像这片土地上的风,升起,带着土地的颜色,和华夏大气的缤纷色泽。
七
今天,中国歌曲是否还存在?它在哪里?它未来向何处去?
其实,中国歌曲不是孤立的,它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的民族歌曲一样,都有着与世界形成之后、全球化泛滥之后流行音乐不同的个性面目。只是因欧陆古典美声、世界流行音乐、摇滚乐——是的,也包括摇滚乐的兴起、坐大、波及,而显形又隐形,明灭在这个世界的听众面前。
未来,包括现在正在发生的,它有着三种面目、三种命运:
第一种,是它在这一场泛及全球的同化浪潮中,被同化一般地显现。同化是其显现的条件,同化又是这歌曲所趋向的结果。由是,它被整齐地置放在美声歌曲、民族声乐、世界流行音乐、摇滚乐的格式里,尤其是集中在世界音乐、新世纪音乐、电子乐、摇滚乐这几种类型之中,成为一种带口音的美声歌曲、民族美声歌曲、世界流行音乐、摇滚乐……
第二种,是被记录、被珍存、被保藏,进博物馆。就像是这世界上存在的生物多样性,这多样性,是历经了地球的历史,天造地设。因为人类主导的大规模的、深刻的现代变迁,多样性受到了毁坏,有的物种,没有了也就没有了,彻底灭绝、消失、不可再生。歌曲也是一样,一种民族歌曲,一旦失传,没有了也就没有了。但是,在某些领域,对某些人,会知道它们的珍贵,千方百计地、上天入地地,寻找它、搜求它、留存它。这是它的第二个命运:作为档案、文献、非物质文化遗产,原生态地录音整理、活化复现、保存下来;也不排除有时候它作为大众的猎奇式文化美食,在音乐市场风行一时。
第三种,是延续和新生,带着其遗传及其变异的所有密码。歌曲不过是现象,它下面的土地、生活、人,才是它的本质。歌曲的形式,不过是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的另一种具形和再现。需要注意的是,尽管世界化极其全面,全球化极其猛烈,但每一个地域的土地、生活、人,带着它的历史、地理、民族内涵,以其母语、器具、生活习惯、地方风尚为载体,又具有延绵力强大的、不被同化的根性。当自觉到这种不同时,便会诞生此地在此时此刻、在新的语境下地方与世界交融的地方歌曲。一方面遗传,一方面变异;其主要面目特征,是有着原本的传统形式、内容,又有着新时代冲击和演化的体例、心性——这是当下生命的最真诚、最真实的表达!